宿州——沧海桑田老汪湖发布时间:2020-05-16 文章来源:
老汪湖,古称陴湖。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演绎着许多历史故事。春秋战国时期的“鲁吴交盟”、秦汉时期的“楚汉战争”、唐朝诗人白居易的“秋灯夜写连句诗,春雪朝倾暖寒酒。陴湖绿爱白鸥飞,濉水清怜红鲤肥。”的著名诗句都和这里交集颇深。
传说很久以前这里并不是湖泊,而是一片繁华的城池,城里街道网如棋盘,楼台店铺鳞次栉比,热闹非凡,人们生活惬意安居乐业。可是不幸一天夜里,突然天昏地暗、电闪雷鸣、狂风暴雨,顷刻之间,整座城池全部塌陷,转眼变成一片汪洋。所以如今居住在此当地百姓仍念念不忘,自豪地说从前我们这里是座“清州府”。
据载老汪湖名籍史册是清同治八年,即公元1869年。《同治徐州府志》载“……界灵璧,据同治八年萧县知县顾景廉勘送县图云:张山(今埇桥区解集乡张山集)东五里九顶山为灵璧界山,南五里大庙圩迤,南有青冢湖,西岸也有湖,南接老汪湖,中有洲曰曹家楼,东里许有三界碑,东北有灵璧,东南有宿,西为萧也,看来这里当时是灵璧、宿县、萧县的交界处。
到了民国时期,因为老汪湖水冬消夏涨,湖水一退便是芦苇荒草遍野,于是就成了无主滩地,所以周围数十里乡民都来抢夺湖滩,经常发生抢滩群殴,枪战械斗不断,死伤事件时有发生,就连县府省府都奈何不得。据说有一年秋后灵璧五区(今游集镇一带)乡民和西邻的萧县十区(今埇桥区褚兰镇)乡民又为抢滩夺湖闹得不可开交,双方县府出面调处不见奏效,眼看就要发生流血事件。当时灵萧两县官方均举荐游集乡绅刘盛荣出面调解。刘盛荣在游集街开有商号“万盛货栈”,乃一乡绅名流。因善秉公办事,十里八乡无人不晓,被外界尊称为“刘圣人”。果然,他一出面,事件很快平息。因为他出门习惯骑驴,所以双方约定:让刘盛荣骑着毛驴,毛驴屁股上绑一袋石灰,以石灰线为准挖沟为界,线以东属灵璧,以西属萧县。刘盛荣此次调处,为游集确权湖滩两万余亩。此后多年两地相安无事。于是游集民间“老汪湖骑驴圈地”的故事广为流传。
近日我走进这神秘的老汪湖游集镇地段,映入眼帘的是万顷良田,绿浪滚滚,庄稼生长旺盛,一片葱茏,满目青翠,清香怡人。我脑际浮现的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的景象。随同普查的刘邦銮(退休副镇长)打破了我的遐想,说建国初期老汪湖仍是大面积明水,湖里芦苇水草丛生,鸥鹭成群,叫声嘈天。后来为了开垦和利用老汪湖的土地资源平衡游集区的土地不足,经县政府协调,给当时的游集区分得了近两万亩土地,被当地人称为“客地”,意思是外乡人来此种地。这里属于无固定收益土地,涝时蓄水、旱时耕种。没有收成保障,正常年份只能收种一季小麦,秋季基本靠不住,可谓是“冬春则涸为平原,夏秋霖潦汇为巨浸”。甚至有的年份全年都有种无收,是完全靠天收成的湖地,所以当时也不用完粮纳税。
据从小生长在老汪湖畔的赵远利先生回忆:“小时候每到夏收季节一过,紧接着便是绵绵的梅雨季节,往往一下就是十几天。倘若雨过天晴,山青水润,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明朗。如若你登临洪山的山顶,立刻便有心旷神怡之感,放眼远眺,郁郁青翠的树林,连绵起伏的群山;东边的茅山水库,波光粼粼,水鸟翩飞。但是最热闹的还要数老汪湖,连日的雨水使老汪湖的水位迅速上涨,此时你漫步湖堤岸边,便可欣赏到水边无际、波光粼粼的湖景了。你瞧,岸边、河坝、小船里、大堤上,到处都是人。老汪湖是蓄水湖,平日里都是干涸的,只有到了梅雨季节,她才发挥蓄水的作用。她没有多大的风浪,显得那么温顺柔美,翻卷的浪花带着微笑,冲向小船,冲向岸边,泛起一层层水花。然而湖水的入口可是另外一番情景,浑浊的河水如同发疯的雄狮怒吼着,拼命地冲击着桥墩,冲击着拦水坝,激起几丈高的水柱,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桥下的水旋转着,那些漂浮的水草、树枝杂物在漩涡中时隐时现,一转眼又咆哮的水中销声匿迹了。”这些就是当年“老汪湖美景”的真实写照。
近十几年来政府着手对老汪湖进行大规模的治理,沿湖边筑圩打坝,加高加宽沿岸大堤,中间挖沟泄洪,兴修了小李庄分洪闸,并对上游奎河水系进行分流改道。经过十几年的奋战和湖区受益百姓的辛勤劳作逐渐把万顷湖泊改造成一片良田。如今的老汪湖已经变成湖岸树木葱茏,湖地沟渠纵横、碧绿滴翠、环境优美、绿波荡漾、旱涝保收的大粮仓。(游传化)
乡镇社区:
- 2025-11-13丁里镇武寺小学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活动
- 2025-09-28薛楼园区开展“巧手制灯笼,团圆迎中秋” 主题活动
- 2025-09-28宴嬉台社区开展三轮车道路安全科普活动
- 2025-08-13苇子园社区开展沿街商铺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 2025-04-22爱心暖夕阳 公益社会组织情系敬老院
- 2025-04-03丁里镇武寺小学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省工商联与宣城市举行工作对接座谈会
省工商联与宣城市举行工作对接座谈会 合肥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姚亚妹一行到合肥市滁州商会走访调研
合肥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姚亚妹一行到合肥市滁州商会走访调研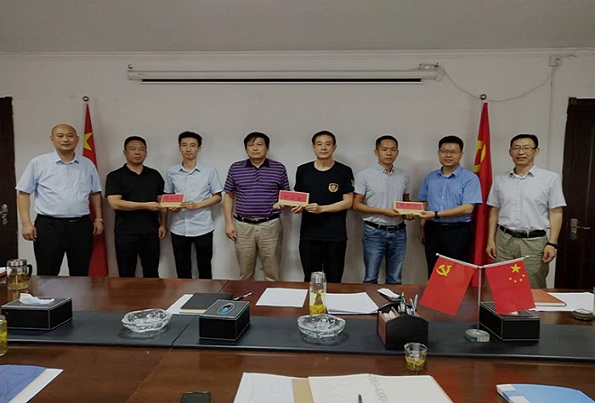 铜陵市工商联开展“八一”慰问机关转业军人活动
铜陵市工商联开展“八一”慰问机关转业军人活动 黄山市工商联到市建筑业协会走访调研并授牌
黄山市工商联到市建筑业协会走访调研并授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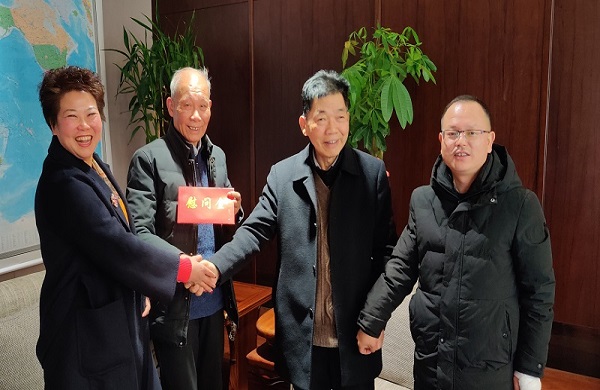 黄山市民协秘书长拜访协会终身名誉会长
黄山市民协秘书长拜访协会终身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