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灵璧县:伏波堂马英将军文化寻踪发布时间:2022-05-26 文章来源:
马英(又名马瑛,下文涉及其名均按所引原始资料呈现,为方便行文,论述时以“马英”称之。下文括号内均为笔者注)何许人也?伏波堂又因何得名?他在灵璧北境马氏族群繁衍发展中居于何种地位?又留下哪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我们不妨以史为证,通过书香氤氲的历史记载来寻找其中的悠远岁月和渐趋模糊的影像。

关于马英相关记载,散见于《明史》《明实录》《北征录》《北征后录》《中都志》《灵璧县志》和灵璧北境申村马氏家谱、马氏祠堂纪事神主碑等史志谱牒碑刻资料。
灵璧申村马氏家族资料主要体现为家谱和神主碑。
据1994年族谱封面“马氏家族分谱第十续谱甲午年戊辰月戊辰日”可知,始迁祖马英定居灵璧(正统四年,1439)之后近六百年中(至1994年)续谱十次。现工作于南京的马氏族人马浩(马修远,始迁祖马英后二十五世孙)提供资料显示,民国三十八年(1949)第九次续谱,民国十七年(1928)第八次续谱。民国三十八年(1949)第九次续谱收录了四篇序言,分别是《大清同治二年(1863)岁次癸亥小阳月下浣二十代孙宗泰序》《大清光绪九年(1883)桃月上浣序》《民国十七年(1928)小阳月(十月)吉日二十二世孙兰新序》《民国三十八年(1949)杏月(二月)二十二世孙兰新重序》。相关资料显示修谱如下:
伏波堂灵璧马氏总谱崇祯末年(崇祯,1627-1644)寇乱失迷;康熙四十年(1700),含英公旁搜远稽,草创初成;乾隆三十九年(1774),廷钧祖重修;嘉庆元年(1796),自道祖重修;道光十六年(1836),元烺、允刚、尚文,三公重修;同治二年(1863),二十代孙宗泰重修;光绪九年(1883),增道重修;民国十七年(1928)二十二世孙兰新第八次重修;民国三十八年(1949)二十二世孙兰新第九次重修;癸酉年(1993,申村泉子长房续谱。申村长房永安祖支系是1993年续十次谱,白马山泉子二房永兴祖支系是1994年续十次谱),第十次重修。其中一次应该在清代,具体不详。而明代修谱情况因总谱失迷于崇祯末,而不得知。据马浩说,民国古谱,目前知道的一共有五部,其中有两本保存完好。
因此,伏波堂马氏申村族谱相关记载因因相袭,传抄补缀,有些信息是可靠可信的。但是限于马氏总谱已于明末崇祯末年失迷,对于马英相关记载是值得商榷的。
根据族谱,马英世系从陕西扶风茂陵成欢里迁居蓟州,因此马英定居灵璧后称祖籍蓟州。因祖上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各地马氏都将他作为本族名人大力弘扬,他们随着时代发展析居各地,依照本支特点命名堂号,如“扶风堂”“铜柱堂”等等,从陕西扶风析居各地以“伏波堂”自称的马氏支系多有存在,如湖北马氏江汉支派“伏波堂”,江苏宿迁马陵山马氏"伏波堂",重庆酉阳马氏“伏波堂”等等。灵璧北境申村马氏始祖马英于明正统四年(1439)定居灵璧,本支本族将“伏波”作为堂号,故而称灵璧“伏波堂”马英支系。
在家谱介绍中,因总谱崇祯末失迷,作为灵璧伏波堂始迁祖马英将军事略则建立在口口相传及零散资料基础上,尤其是马氏祖茔马英墓碑及祠堂神主碑信息。家谱和民国四年神主碑中言,马英祖籍蓟州,官至明前军都督府佥事(根据《明实录》记载,这不是马英最高官职,其最高官职为五军都督府后府右都督,正一品)。立过两次大功,一是靖难之役,灵璧齐眉山之战时红桥救驾,二是征讨交阯(治所在今越南河内),杀敌立功。关于第一点“红桥救驾”,查阅有关史志书籍没有这方面明确记载,但有关史料表明,马英全程参与了靖难之役,并立下赫赫战功,以致明成祖朱棣攻占应天府(今南京)后升马英为浙江都指挥使,正二品,不久调入五军都督府,任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第二点,《明实录》相关史料表明,征讨交阯时,总兵官王通私下议和、擅自丢弃交阯城违抗皇命而受到处理,马英受其连累,后罢官为民而隐居灵璧十年至去世。马英在交阯征战中,依然立下军功。家谱记载虽有所讳饰,但有相当真实性。马英受到连累不仅值得同情,更值得惋惜。这种际遇更坚定了马英归隐林泉,远离纷争的内心深处信念。当然,这也是传统意义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并弘扬一方正气的古代官员追求之体现。马英虽为武官,骨子里仍然浸透传统文化的精髓。
马英事略可以从《明史》《明实录》等资料中一见究竟。。
作为明朝前军都督府佥事(民国四年神主碑、《中都志》、康熙版《灵璧县志》信息),朝廷正二品,马英应该在《明史》中留下传记,然而《明史·列传》中却无其传。原因在何?这可能与其罢官隐居淡出人们视野有关。清代编修《明史》时对其忽略令人不解。但是作为一员靖难之役、北征蒙元残余和征讨交阯中驰骋疆场的大将,必然在正史中留下深深印痕。
《明史》记载有五处,其一,卷九,本纪第九,宣宗,“(洪熙元年,1425,秋七月)闰月戊申,安顺伯薛贵、清平伯吴成、都督马英、都指挥梁成帅师巡边。”其二,卷一百六十,列传第四十八,王通,“[宣德元年(1426)冬十一月]会通至,分道出击。参将马瑛破贼于石室县。通引军与瑛合,至应平之宁桥中伏,军大溃,死者二三万人,尚书陈洽与焉。”其三,卷一百六十,列传第四十八,王通,“明年(1428),通还京,群臣交劾,论死系狱,夺券,籍其家。正统四年(1439)特释为民。景帝立,起都督佥事,守京城。御也先有功,进同知,守天寿山,还其家产。景泰三年(1452)卒。天顺元年(1457)诏通子琮嗣成山伯。琮子镛,成化时赐原券。传爵至明亡。”其四,卷三百二十一,列传第二百九,外国二,安南,“宣德元年(1426)春,帝敕沐晟剿宁远,又发西南诸卫军万五千、弩手三千赴交阯,且敕老挝不得容叛人。四月,命成山侯王通为征夷将军,都督马瑛为参将,往讨黎利。……马瑛败贼清威,至石室与通会,俱至应平宁桥。士卒行泥泞中,遇伏兵,大败。尚书陈洽死焉,通亦中胁还。”其五,卷三百二十一,列传第二百九,外国二,安南,“(宣德)三年(1428)夏,通等至京,文武诸臣合奏其罪,廷鞫具服,乃与陈智、马瑛、方政、山寿、马骐及布政使弋谦,俱论死下狱,籍其家。帝终不诛,长系待决而已。骐恣虐激变,罪尤重,而谦实无罪,皆同论,时议非之。廷臣复劾沐晟、徐亨、谭忠逗留及丧师辱国罪,帝不问。”
《明史》中有关马英记载,主要集中在其洪熙元年(1425)春由五府之后府都督佥事升为后府右都督之后。闰七月,马英率领军队巡防北方边境。然后宣德元年(1426)冬十一月在总兵官王通节制下,开赴南方边境,平定交阯之乱。兵败返回北平遭弹劾直至罢官为民及朝廷下诏启用并荫封后世。有些信息不清,而升任后府右都督之前事迹缺失。
相比之下,《明实录》有关马英记载则较为详细。
《明史》中五处有关马英史实均能在《明实录》找到佐证,《明实录》中直接出现马英(瑛)名字共有十八处,间接信息则有多处。所叙述的史实也更为丰富。
根据史实,最早见于《明太宗实录·卷十二》,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朱棣即位后,不承认建文,以洪武纪年纪之)九月,马瑛升为浙江都指挥使。查《明史》职官知,都指挥使为正二品武官。而根据《明太宗实录·卷十八》,永乐元年(1403)三月,马瑛因朱棣念及靖难之初攻占北京九门之功,升为前军都督佥事。都督佥事在明朝武官序列中也是正二品,但是它进入到最高武装力量指挥中心,离皇帝和朝廷更近,当然是一种升迁和恩荣。这里还透露一个信息,那就是马英不在建文帝武装阵营中,不是后来投降朱棣或半路参加朱棣军队,而是朱棣的嫡系,因为马英参与了对于朱棣来说最为关键的夺取北平九门行动。这是靖难之役的开端。“[建文元年(1399)] 秋七月癸酉,匿壮士端礼门,绐贵(都指挥使谢贵)、昺(布政使张昺)入,杀之,遂夺九门”(《明史·卷五·本纪第五·成祖一》),短短三年,建文四年(1402),马英即成为浙江都指挥使,正二品。可见,马英在靖难之役过程中立下功劳之大。可以说是夺取北平九门之八百壮士中佼佼者,其武功谋略和指挥能力出类拔萃。马英作为东汉名将马援后裔,习武报国的因子已深入其血脉骨髓。还可以进行合理的推测,马英在此之前,跟随朱棣镇守北平,与北方蒙元残余势力殊死搏杀,早已由一名基层士卒成长为朱棣手下心腹干将。马英生辰由此可知,大致在明朝建立前后。其在明初北方动乱中继承家风,习武报国,在朱棣镇守北平时参军搏杀,快速成长。靖难之役中立下军功,朱棣占领南京后(1402)晋升为浙江都指挥使,永乐元年(1403)又恩赐前军都督府佥事。
其后,永乐十一年(1413)夏四月,马英以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身份和都督程宽、何璇率舟师运粮赴北京。永乐十二年(1414)二月,马英以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身份,与兴安伯徐亨、章安作为副职,受中军都督府武安侯郑亨节制,到兴和营操备,准备跟随朱棣二次北征,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朱棣第五次北征返京途中驾崩。八月,马英被熙宗由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调任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并勉励其作为先朝勋旧,要继续无愧职守。
那么从永乐十二年(1414)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驾崩,马英一直担任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其间,他都在履行何职责?经历了明朝哪些重大事件?
从《明史》可知,明初明朝所面对的挑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北方蒙元残余势力侵袭;二是南方交阯与中原王朝的对抗。对于北方蒙元残余势力,朱棣时期进行了五次北征,分别在永乐八年(1410),北征鞑靼;永乐十二年(1414),北征瓦刺;永乐二十年(1422),北征鞑靼;永乐二十一年(1423),北征鞑靼;永乐二十二年(1424),北征鞑靼。而在南方,先是派成国公朱能、四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丰城侯李彬、云阳伯陈旭,督师南征。朱能死后,张辅统领南征大军。张辅回京后,李斌代统。李斌死后,荣昌伯陈智代替。直至宣德元年(1426)春,王通佩征夷将军印,充任总兵官,马瑛以后府右都督身份任参将,往讨交阯叛贼黎利。在此期间,马英一直效命北方,或五次跟随成祖朱棣征讨北方蒙元残余势力,或镇守北部边境。朱棣五次北征,因蒙元残余势力躲避决战,收效不显,这也是马英多年一直未能升迁的基本原因。而后来洪熙元年(1425)春正月,马英才得以五军都督府后府都督佥事升为本府右都督,正二品武官成为正一品武官,半年之后,洪熙元年(1425)闰七月,马英以后府右都督身份和安顺伯薛贵、清平伯吴成、都指挥梁成等率兵巡防塞外。宣德元年(1426)夏天后,北部军事集团南征,与北征未能斩草除根共同为北方蒙元残余势力壮大留下严重的后患。
马英升迁五军都督府后府右都督,迎来他人生中高光时刻,但也从此步入其人生的至暗时代。因为他遇见了王通。但是马英依然英勇不减,军功可圈可点。
宣德元年(1426)冬十一月,马英以后府右都督身份充任参将,在总兵官、成山侯王通等进兵击贼大败情况下,到清威与贼遭遇,大败清威贼兵,到达石室县和王通合兵一处。宣德元年(1426)十二月,马瑛按照皇帝命令,和交阯总兵官成山侯王通一起,固守城池,操练军马,等待安远侯柳升、黔国公沐晟等率军从广西云南两路并进,一同进兵。
然而王通先期轻敌,不等援兵到达,擅自出兵,得胜后又未能乘胜出击,扩大战果,为事官陈智、李安、方政、布政使弋谦和内官山寿、马骐等擅行其事,以致交阯贼兵死灰复燃,形势出现反复。朝廷任人失察、互相牵制、指挥混乱等因素也是失败的深层原因。在此情况下,王通等人不设法弥补挽救危局,却私心作祟,宣德二年(1427)十月,擅自和交阯叛贼黎利订立盟约媾和,双双罢兵,互赠物品。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朝廷专门下令,要等班师回朝命令到达才允许回师。王通不等命令到达,宣德二年(1427)十二月,撤离交阯城,退回广西南宁,马英亦随同退回南宁,导致藩属国交阯事实上的独立,这也是当代中越形势的肇始。王通事实上负有重大历史责任。
朝廷对于交阯事实上的独立无可奈何,只能立足当下形势,承认既成事实。宣德三年(1428)闰四月,马瑛同成山侯王通、内官山寿、马骐等带领隶属京城官军回还京师后,遭到文武群臣弹劾,马瑛同王通一起被罢免为普通百姓。
马英何去何从?成化六年(1470)纂修的《中都志·卷之五·人才》载:“灵璧县,国朝,马英,固镇保人,任前军都督府都督签事。”削职为民后,马英以平民之身迁居到凤阳府宿州灵璧县固镇保(今安徽省固镇县城关镇),故有《中都志》记载。根据康熙版《灵璧县志》(卷四,秩官志)载,固镇当时设有巡检司,并有驿站,水通淮河,陆达京师,亦有集市。同时,固镇隶属灵璧,灵璧既是朱棣小河(睢河)对峙险象环生之处,又是齐眉山之战发生地(此战中朱棣战败,危机中转危为安,朱棣认为是城隍护佑,故封灵璧城隍为州等级),更是灵璧之战大败南军的关键战场,朱棣对此留有深刻而复杂记忆。马英安家于此,除了固镇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外,未尝没有个中的考量。由此可以看出,马英一定参与灵璧几次关键战役,对灵壁情有独钟,并留下好感。当然,马英定居于此,更与其骨子里山水情怀有关。这在其给两子取名可见一斑。马英长子马林(又马麟),次子马泉。一林一泉,合则为“林泉”,隐隐透露出马英遁世之山水情怀。尤其是历经战场拼杀见惯生死,年届七十,远离北方祖籍征战之地,定居灵璧固镇保成为其自然之选。
马英遭遇是明朝内忧外患大背景决定的,时势使然。但是,马英受到不公平对待,却能以大局为重,坦然面对现实,离开朝堂,隐居乡野,展示了豁达自然的赤子情怀。重新启用、荫封后裔、遣官致祭、耕读传家、弘扬一方正气而繁衍生息,这也是冥冥中天道正义对马英及其后裔最好的回报。
本以为就此终老固镇,可是马英这批当年跟随朱棣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老臣,在忠国公石亨等昔日同僚斡旋下,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英宗重新任命王通为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提督守备九门。在征战瓦剌部也先时立下战功,朝廷归还其家产。
王通等人重新得到重用,马英时已八十岁左右。据申村马氏后裔传说,马英因皇帝诏命到达,不知内情,以为杀身之祸降临,惊吓过度而逝。如果此传说属实,马英应是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去世。《明史·卷一百六十·列传第四十八·王通》有“(王通)景泰三年(1452)卒”信息,马英逝于正统十四年(1449)较为可信。马英在固镇保至少生活了十年。马英靖难之役跟随朱棣征战灵璧,对此地风土人情较为熟悉,十年间寻找合适墓地,便看中灵璧北境凤山南麓,那儿依山望水,风水绝佳,得天独厚。据马氏后人说,马英逝后,朝廷恩赐五十八亩土地修建和维护祠堂,并遣官致祭。石碑为蛟龙碑,历经明、清、民国至现在换过几次碑,坟冢墓碑于1968年毁坏(据祖茔东侧一位八十多岁老太太说,马英墓前古碑以前没动过,墓碑很高,有碑帽,碑前有石供桌、香炉、石狮子。现存民国四年修缮祠堂所立神主碑,当时砸碑时,时任族长马春德把这块神主碑翻过来藏在桥下躲过劫难)。
那么,马英族人迁居灵璧县固镇保后,又是何时迁居灵璧北境陵子镇(今安徽省灵璧县浍沟镇后灵村),迁居到凤山南畔申村?因何迁徙?根据家谱载,始祖马英后六世马荣已居灵北申村,家谱中明确“祖居陵子”。由《中都志》编纂时间为成化六年(1470)马英为固镇保人,可以推测,应该在马英去世不久,马英葬于凤山之阳青豸山(申村山)下,最晚成化六年(1470)《中都志》编纂时,马氏族人是居住于灵璧县固镇保的,当然更有可能,马氏族人二世迁居陵子,而《中都志》录马英时,以马英被削职为民后移居固镇并在固镇生活了十年,溘然长逝,逝后葬于凤山之阳,将固镇保作为马英籍贯。而康熙版《灵璧县志·卷六·选举志·武秩》(成书于康熙十九年(1680))载,“明,马英,固镇保人。以功历前军都督签事。见《中都志》。”可见,康熙版灵璧县志照抄《中都志》。虽马氏家族早已离开固镇保,来到陵子镇,又来到申村,但县志依然遵照《中都志》记载马英初始迁居地而录。
马氏族人在马英逝后迁居陵子镇,至少在五世时又陆续迁于申村祖茔之畔。
成化六年(1470)纂修《中都志·卷之四·坊市街巷乡村都保镇》中有灵璧县“陵子集”,“陵子镇”。陵子在当时不仅是物质转运交易之所,也是驻兵防控的地方。陵子处于睢河北岸,又是北方物质南下的要地,工商业较发达,经济较繁荣。陵子,北近马氏祖茔之地,交通便利,便于经营生存。马英后世应该二代后迁居于此。但陵子处于睢河及北来河流交汇处,上游都较深阔,陵子之后,泥沙沉淀,河床抬高成为低洼广阔之处,多受水涝之苦。因而睢河至此,又称陵子门。乾隆版《灵璧县志略·卷一·山川》中“湖名以百数,杨疃、土山、陵子、孟山、崔家是为五湖,其最著已。陈志皆无之,盖当时尚未成湖也。”“陈志”为万历末灵璧知县陈泰交纂修《灵璧县志》,即万历末灵璧北境尚无五湖。作为水流交汇之处,在马英二代迁居陵子后当然要遭受水涝之苦,遂于三四代又迁居申村,居于祖茔之畔。申村处于申村山南麓,地势高昂,山峦绵延向前直至睢河,多山地平原耕种之地。于是,这儿便成为马氏长久居住之宝地。古代,生产力落后,人们改造自然能力低下,常常逐水而居,居住地而市,而城,又因水涝或水竭而弃,水映照着人们迁徙的身影。
其实马氏后裔居于灵北凤凰山(申村山)南麓,一个疑问自然产生:马氏自明初迁居于此,为何称申村?叫马庄或马村或马寨或马城等等不更适合吗?这里还有一个家族故事。
据政协灵璧县委员会编《灵璧地名文化》(上册,黄山书社,2019.12)中《凤山脚下凤山村》《申村无申姓由来》《马家古寨与马尔顾》《伏波堂里马英祠》四篇文章可知大概,虽说传说成分居多,但其真实性加之遗存佐证尚有很大可信度。
申村位于灵北凤山南麓。凤山又名凤凰山,因申村,康熙《灵璧县志》称之为申村山,西连开合山,东接二王山、熊桥山,自西向东蜿蜒成一道天然屏障。凤山东部高耸,宛若凤头,凤头以下向西,渐趋平缓,形如凤凰双翅张开,渐而成为凤尾,天然一方风水宝地。马氏祖茔即处于凤凰胸部俗称嗉子处。凤山之东亦产“万卷书”石,是古代皇家制造石磬的难得石材。乾隆版《灵璧县志略·卷一·山川》言:“潼山(潼水出焉,山北庄姓祖茔有古树一株,扶疏可爱):潼山西南曰无影山(山卑,四面受日光,故名),其东曰开合山、申村山、土龙山(产黑白石)、周家山(产纹石)、红鸟山(产透花石),皆在县治正北连延十五六里,如列屏障。去县治可七十里,山后冈阜林立,有曰杨家山者,有曰白马山者,有曰卓山、辉山者(二山之石亦可为磬)。辉山与红鸟南北相值,山势至此一断,而石磬山耸峙于东矣。”凤山中部,水流无数年冲刷,形成一条宽约十米、深约五米的水沟,名曰“龙抓钩”,又曰“劈山沟”。此沟冬春无水,夏秋雨季水流湍急。
申村居于凤山南麓,北临凤凰山,南临季节性湖地,北半山南半湖。夏季多雨年份,山洪暴发,湖地变成湖泊。夏季少雨之年,则成湖地。因此旱年湖地保收,涝年山地有成。申氏来此居住已久,明初因太过张扬,打响场而惹怒官府,招来杀身之祸,申氏族人被迫砸锅分锅离析各地,申氏故称“破锅申氏”。马氏族人渐渐迁居固镇保、迁居陵子镇,迁居凤山南麓申村。
马氏家谱云,总谱于崇祯末年寇乱迷失。查康熙版《灵璧县志》(卷一,方舆志,城池)知,天启二年(1622)至崇祯九年(1636),“流寇陷城者三”。崇祯十年(1637)知县王世俊亲率市民加高城墙,疏宽护城河。流贼攻城失败。当时,乡绅王守谦八旬有余,登城率子孙守城,激励士气。流寇在明末多次劫掠灵璧,一度闯入灵北申村,以至马氏宗谱迷失。鉴于此,马氏遂于祠堂祖茔之东修建庄寨,即马家寨。
申村中马家寨也是村庄形成中的一个奇观,隐隐透露着两个不同姓氏族人迁徙的背影。马家寨初建于明末,主要为了防护兵匪,保家安业。乾隆年间,连续多年丰收,于是马氏族人修缮祠堂,又加固圩寨。方圆纵横八百米,寨墙为山上巨石垒砌,宽一米,高七米,墙头有垛口,四周有瞭望口。寨外有壕沟,宽八米,深三米,水下有暗桩,铁钩相连。壕沟土方运至寨内墙下,加固墙基,便于登墙防守。寨四角有敌楼,内有土炮等防御武器。马家寨有南北两寨门,寨门旁设有护门暗堡。北大门为正门,门楣上嵌有青石板,宽零点六米、高两米,上镌对联,“伏海征南安天下”“波卷诛北定太平”,横批“伏波遗风”。南寨门亦有青石板对联,“雁过重门留好语”“莺啼绿柳报新春”,横批“胜似春光”。
马家寨成为乱世马家族人和临近百姓的心理寄托和生存依靠,亦是马氏尚武精神、保家卫国遗风的写照和流传,自建成后,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1938年和1942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1938年,渔沟土匪相约遂宁歹人偷袭马家寨。千人之众七天七夜未能攻下,损失惨重,甚至总头目都被射杀。马家族人及邻近村民躲过一劫。1942年,灵城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县长许觉远等搬至马家寨。日军在飞机轰炸下攻击马家寨,马氏族人在马兰春率领下,誓与圩寨共存亡,和日军逐巷逐屋拼杀,除少部分人突围外,众多马氏族人壮烈殉国。马家寨遂损坏。
马家寨依然留存着历史和文化的痕迹。申村三组和四组间有条八百余米的南北浅沟,时光流逝,几乎填平,谁曾想到那是圩寨东面的壕沟?四组西面壕沟,断断续续,依稀可见当年的影像。而寨南壕沟上早已建满房屋,北面壕沟成为村里东西大路。村人回忆,二十余年前,寨南门地基还见遗迹,浮雕着麒麟、云朵的门枕,砸坏的石狮子,刻着图案的圆鼓形石器,旗杆座,仍见踪影。一些老屋、废弃宅院边还能看到雕刻精美的石板、刻有笄形兽纹的石块。北门是寨圩主门,石雕丰富,现在踪迹不见。马家寨作为马氏族人曾经的记忆,虽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却在马氏族人记忆深处闪着熠熠光辉,它们早已成为马氏族群生生不息的文化符号流淌在人们的血脉里。
马英逝后八年,其长子马林支系迎来荫封。(夺门之变后)英宗重新登上皇帝宝座,天顺元年(1457)七月,王通去世五年之后,忠国公石亨等人向曾经的英宗如今的天顺皇帝奏请,天顺皇帝恩命成山候王通的儿子王琮承袭成山伯。天顺元年(1457)十一月,“至是,通子琮遇赦袭伯爵,骘援例奏请,故有是命”。明代实行卫所军户制度,武官世袭。马瑛的孙子马骘依照王通的儿子王琮遇赦承袭伯爵先例,请求袭封。英宗皇帝恩命同意贬谪为民的原后军右都督马瑛的孙子马骘,袭承为羽林前卫指挥同知。这也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马英长子马林(麟)业已去世,故而命长孙马骘袭封。马英罢官为民,荫封后裔,这里不仅有皇权之间的斗争,还有靖难之役功臣派系与后起之功臣权贵之间的斗争。这场际遇的结果,对于马英而言,无疑是较为公平的,也较为幸运。
马英长子马林(麟)大概率没有受到其父马英罢官为民影响。《明史·卷一百七十三·列传第六十一·石亨》载:“(正统)十四年(1449年),(石亨)与都督佥事马麟巡徼塞外。”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944)《蓟县志·卷二·官师》载;“马麟,灵璧人。以金吾卫指挥使掌蓟州卫事,果敢有为,军士赖之。其孙瑄读书尚礼,助木植修文庙。瑄子守备遵化,上下交誉,侄恺亦任参将。”中华民国三十八年(1949)续修申村《马氏宗谱·始祖传》载:“(马英)长子讳林,因父屡建大功,封荫袭锦衣指挥,从成祖北征,居蓟州遵化县,世有禄秩。” 马林受父亲马英熏陶,亦从军,并参与成祖北征(从大致年龄上推测,应该是第三、四、五次北征)经过多年刀光剑影历练,逐渐成长为镇守北部边境的大将,因军功官居都督佥事,正二品。马林和当时朝中炙手可热的石亨配合巡防塞外,曾经以正三品金吾卫指挥使掌管蓟州卫事,果敢有为,深受士兵们的信赖拥护,累功至正二品都督佥事。马林去世后归葬灵璧申村祖茔马英东北畔。其后裔便居于马林为官之地蓟州遵化。马林之孙、马骘之子马瑄弃武从文,读书尚礼,捐助树木,修缮文庙,赢得地方赞誉。马瑄的儿子又回归武行,守卫遵化,人们交口称赞,马瑄侄子亦升职参将。
马英爵位在蓟州遵化马林长房世袭,马英次子二房马泉支系便于灵璧北境凤山南麓申村耕读持家,繁衍生息,延续香火,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冬在马英祠基础上修建宗祠,竖立始迁祖马英神主碑,敬立祖宗牌位,供奉祭奠马英等祖先。
马氏宗祠,又称马氏申村祠堂,新中国建立后,宿州市文物普查时称为“凤山祠堂”,位于申村祖茔之北,距祖茔300余米。据当年最后一代护墓老人的儿子马新才(现年95岁,身体健康。其祖上自山东逃荒来申村,为马氏看护祠堂。祠堂周围土地收入及每逢祭祀等活动供品归其祖上所有,以供生活所需。现马新才子孙满堂,生活幸福,对马氏祠堂等怀有别样情怀)回忆,马氏宗祠建在申村山(马氏家谱中之青豸山)半山腰,大殿三间,殿前有十八级台阶,殿前左右有旗杆座,辟邪兽等大型石雕和记事石碑等。大殿条石奠基,青砖砌墙,小瓦鳞次,山墙高耸,挑檐翘角。山墙脊顶,东西两头各立一株红铜铸造插花树,约三米高,树上有鸟,鸟张嘴巴,似在鸣叫(明清古建筑称之为“插花云燕”)。大殿东西两间向南,各建一间庑房,紧连大殿却不相通,独立向南开门。这叫“二郎(廊)担山(三)”。据说插花树、开嘴鸟儿和“二郎担山”架构是有功名的家族才允许建的祠堂样式。大殿里古木榫卯相接,雕梁画栋。正殿对门墙上,挂着始迁祖马英将军画像,马林、马泉陪侍左右。画像下是宽大的供桌,上面有神龛,陈列着马氏历代列祖列祖神主牌位。正殿正中立着马英神主石碑。大殿南侧东西两旁有厢房,每边有五间。西厢房可以做饭,东厢房可以居住。他乡马氏族人回到祖祠祭祖认亲,有时一住两三月。厢房再向南,连接着大门,大门门楼耸立,榫卯结构,亦是挑檐翘角。门楣上“伏波堂”三个大字熠熠生辉,近看,庄严肃穆,古朴大气。远观,巍峨壮观,气派非凡。大殿四周明代栽植松柏,郁郁葱葱,特别是东面,松柏高大,浓阴匝地,百鸟和鸣。马氏祠堂尽显中国古代将军家族宗祠的威严厚重,浓缩着家族文化的精华,寄托着铭记根本、弘扬团结和耕读持家的家族精神,这种宗法制度和精神稳定着地方社会,支撑着国家大厦。
20世纪30、40年代,申村马氏宗祠,成为中共地下联络点和军事指挥所,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奉献力量。50年代初,这儿设立申村小学,高小五、六两个年级,艰难岁月,为提升国民素质发光发热。直至1968年特殊年代遭到破坏。
马氏申村祠堂向南,便是马氏家族祖茔。马氏申村祖茔在中国墓葬形制中别具一格,即“驮孙葬”。
中国古代墓葬格局主要有三种,即“抱孙葬”、“排孙葬”和“驮孙葬”。“抱孙葬”又称“携子抱孙”葬,是最流行的一种墓葬格局,始迁祖墓后不留空间,墓前空间广阔,留给子孙后代墓葬。如曲阜孔子以下三代即是典型的携子抱孙葬。“排孙葬”则始迁祖墓前留存大量空间,子孙后世按代一排排埋葬。而“驮孙葬”始迁祖墓前不留空间,子孙后代在始迁祖墓后以辈次排开。二代左长右幼,三代以后,内长外幼。这常见于公侯将相家族墓地葬法,在我国葬式格局中具有典型意义。
灵北申村马氏“驮孙葬”墓地,马英墓居于最前,其后左为马林墓,右为马泉墓。马林后裔居住马林为官之地蓟州遵化,逝后亦埋葬于遵化。按照申村说法,现申村祖茔之东即是为马林后裔所留墓园,已被原山东逃荒到来为马氏看护祠堂祖茔的人家建房居住。马泉后裔,八世之前,围绕马泉西北展开,九世至十一世,便按照内长外幼及东长西幼格局埋葬,当然马英之后除马林世系外,至十一世,有析居申村之外和外出无音信者。十一世之后,马氏后裔也就不再葬入祖茔,而是因地因时而葬了。祖茔内每座坟前都有墓碑,镌刻着每个人的生平功绩。墓碑均与1968年砸毁。马氏祖茔背依申村山,正寓子孙步步高升之意。前方明堂有山脚之水,有睢河东流五湖之水,乃风水学上绝佳之地。马氏申村祖茔作为古代正一品将军墓园以十一代汇聚于此并保存良好很是罕见,实在是我国古代高级武官家族墓园“驮孙葬”的难得遗迹,具有深刻的传统文化价值。
马英优良家风深深镌刻着马氏后人的品行,马氏后人为人正直,造福乡里,其后世出现明代中期家资数万黄金的六世马荣,留下“南吴北马”之时谚,并且“家资与诸舅均分”,传为一时之佳话;有明后期嘉靖天启年间的十一世马岱,心公性平,仗义疏财,嫉恶如仇,族人亲邻无不敬服;马岱长子十二世马一骅,擅长诗文,以善道教人,弘扬良好家风;
马一骅次子十三世马之劲,是廪膳生,却不屑功名,善书写,又好弈棋,热心善事;十六世马自道,邑庠生,重视传送家谱,弘扬一方和谐平安;更有明清之际的星象家马尔顾及清代十六世增生员马自治、十六世马自善、二十世廪生员马宗泰等等地方名流。近代以来,尤其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出现了近百人英雄群体。
马英入世慷慨赴国难和出世耕读扬正气的家风,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重要构成部分的家族文化深深滋养着马氏族人,滋养着我们这个民族。马氏祖茔“驮孙葬”遗迹也将以难得的文化遗存见证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伏波堂马英将军谱系文化作为社会生活最基层的家族文化,以共同的血缘纽带、地域性和社会观念,在构成整体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民族演进中,彰显着独特的魅力。透过时光的遥远可以发现马英申村家族迁徙的曲折轨迹、流动的时代背景和生存抗争的内在品性,更可以观照中华民族古老中国的坎坷起伏、源远流长。
同时,这种独特的谱系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厚重的“家国天下”思想,并以其传统内在特质,彰显着深刻的时代价值和社会意义。(牛士中)
【责编:陈嫚】
乡镇社区:
- 2025-11-13丁里镇武寺小学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活动
- 2025-09-28薛楼园区开展“巧手制灯笼,团圆迎中秋” 主题活动
- 2025-09-28宴嬉台社区开展三轮车道路安全科普活动
- 2025-08-13苇子园社区开展沿街商铺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 2025-04-22爱心暖夕阳 公益社会组织情系敬老院
- 2025-04-03丁里镇武寺小学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省工商联与宣城市举行工作对接座谈会
省工商联与宣城市举行工作对接座谈会 合肥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姚亚妹一行到合肥市滁州商会走访调研
合肥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姚亚妹一行到合肥市滁州商会走访调研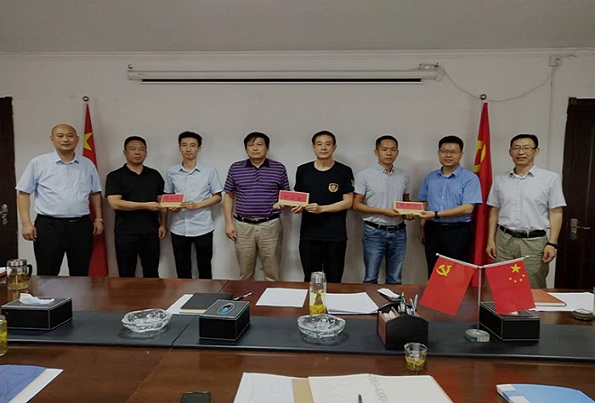 铜陵市工商联开展“八一”慰问机关转业军人活动
铜陵市工商联开展“八一”慰问机关转业军人活动 黄山市工商联到市建筑业协会走访调研并授牌
黄山市工商联到市建筑业协会走访调研并授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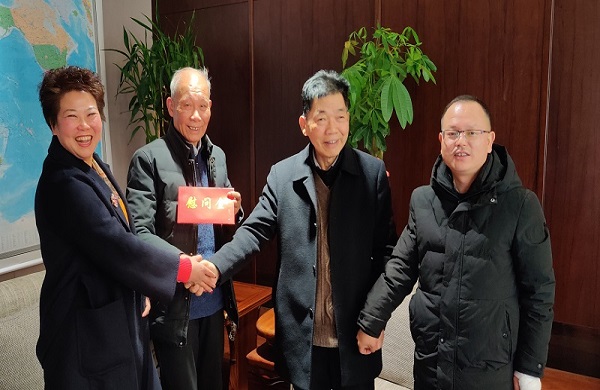 黄山市民协秘书长拜访协会终身名誉会长
黄山市民协秘书长拜访协会终身名誉会长